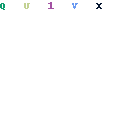自从爸生病以来,整个人仿佛迅速进入了老年期,总是说起他年轻的时光以及那些远去的人和事,说的最多的是山西的老家山西省忻州市定襄县那个叫南王村的地方,说起爷爷16岁时带着太爷太奶走西口来到内蒙,那一场声势浩大的逃离和劫难。他说想回山西看看,从前是为生活奔忙,现在闲了,身体却不大好了。为了了却他的这份夙愿,我和弟弟计划好了今年春天一定带他回去看看。
机缘巧合的是,在我大爷出殡的时候偶遇到一个帮忙的师傅,山西人,一攀谈,竟是一个村的老乡。老乡很激动,当即拿出200块钱,硬塞给我爸,说来内蒙20来年,第一次遇见本村人。问爸老家还有什么亲人,爸说,只有一家叔叔叫周仁文,恐怕早已过世,他的子女应该在,名字依稀记得,一说,还住前后院。很快给要来了联系电话,电话打通,都非常激动,是仁文爷爷的二儿子,我的二叔,他用浓重的山西话说:是了,我家口外是有亲人了。
当我和弟弟、妈妈陪着爸爸一路东南向老家进发时,一路上的盘山路和遂道他不时感慨着,这路步行着走西口出来,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好的体力啊!这是他第一次回去老家,心里充满着各种期待,一路上身体状况非常好。
如果不是生活极度困难的农民,一般是不会想到要离开自己家乡和土地的。当年那一场艰苦的大迁徙——走西口,带给他们太多的苦累,甚至是鲜血,而带给我们走西口人群后代们的生活可以说都是益大于弊。因为亲眼见识了老家目前生活的简朴,便愈加感谢自己的老先人们能走出来的大局心态。因此,也对爷爷他们走西口这个伟大的壮举充满了感恩之情。
爸爸说爷爷常说起,从山西来口外现在的家需要走9天,回去要走11天,因为回去时买了毛驴,要把赚来的钱物都带回去,相对就慢了些。后来,因为途中总遭土匪抢劫才决定定居内蒙,这也是我们目前得以在内蒙生活的原因。我是之前就去过山西的,的确比较穷,人多,地少,就算正常讨一口吃喝都是不容易的。尽管现在山西也是煤炭大省,但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依然不富裕。
爷爷来内蒙的时候很年轻,太爷他们是耍木匠手艺的匠人,来了内蒙,靠这个手艺开了15间木匠铺,现在看来那规模相当大的。生活本来已很不错了,爷爷也在口外娶妻生子,有了大伯和二伯。不幸的是,日本人打到内蒙时飞机轰炸时,爷爷带俩孩子躲了起来,太爷和太奶被日本人飞机投下的一颗炸弹正炸在怀,待爷爷回家时,爹娘的胳膊腿扔了一院子。木匠铺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各种工具、木料拉了8卡车。所幸木匠铺里和太爷一起的合伙掌柜,我的老爷爷幸免于难。还有爷爷的第一任妻子那一年因病去世,家中那一年五口至亲的人过世,还有他的一个孩子和一个离家在外的兄弟。爷爷一年中彻底老去,精神也差点崩溃。加上年轻时曾经给王爷家牧马时套马摔下来落下的全身疼痛的老毛病,后来,落下了睡梦中总是呻吟的毛病,爸爸讲起,呻吟里夹杂着老家方言喊妈妈bo呀bo呀。那呻吟里的痛楚有精神和身体双重的疼痛,这呻吟是痛苦忍受到了极端的出口,但却不敢大声,支撑着他醒时的坚强......
车子一路奔波到了村口,爸和迎上来的二叔手握在了一起。回家里坐下来拿出老人的照片时,爸拍着照片和桌子激动地说,就是就是,没有认错,这下确信了。接下来开始了漫长的回忆。
他们说起了爷爷那最艰难的一年,被飞机炸死的太爷太奶、还有爷爷去世的原配妻子和无人照料的大伯二伯;以及和爷爷相依相助的没有一点血缘关系的老爷爷。老爷爷一直在我家生活到终老,没有成过家,膝下无儿无女,是爸爸他们为他养老送终的。老人家对我们全家有恩,对我,更是有恩的,他把我带到4岁的时候,不会叫我的名字瑞瑞,只会叫肉肉,不给大娘他们看孩子,只看我。至今我还依稀记得他满头的白发,临去世时盖着大红的被子。后来他老人家被葬到了爷爷的坟旁边,每到时节,全家人都会一起去祭拜。他们也说起了我的奶奶,她是姑姑、爸爸和四叔的亲妈妈,一位精明的老太太。还说起山西二叔的爸爸,也就是老家的这位仁文爷爷,他是八路军出身,写一手好字,在乡里工作过,但从未要求政府安置过子女,两儿子至今生活在农村。在我的奶奶去世后,仁文爷爷从山西带了一个无儿无女的我的小奶奶到内蒙,她一直陪伴我爷爷走完人生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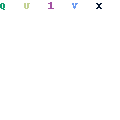
爷爷走时才60岁,爸说,他苍老得像80多岁;爷爷,是被那时大起大落的艰难日子打击老的。山西的仁文爷爷是因癌症去世,走时也才61岁。老弟兄俩都早早离世,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承受苦难的肯定不止我们一家,但我们家可能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家,因为走西口,爷爷不仅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产业,更在一年间失去了至亲的五口家人,走西口的苦和泪不是用语言能讲述完的......
二叔那天稍喝了点酒,和爸兄弟俩越说越激动,完全沉浸在过去生活的回忆中,二叔还说起了内蒙古包头的一些老地名,他8岁那年来过一次。
包头有我的老姑姑,和爷爷也没有血缘关系,是爷爷奶妈家的女儿,也是从山西老家走西口到包头的生意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晋商。老姑父做丝绸布匹生意,就在生意鼎盛将要扩大店面时,然而,一天晚上,他老人家回家坐下来算帐时,被包头街上的混混因为看上他的貂皮帽子,争抢过程中用顶门的棍子当头一棍下去,老姑父没能再醒来。那时他们还没有孩子(老姑夫死后,老姑姑从教堂里抱了个男孩子,也就是我的大爷),老姑姑很年轻,原来从不插手的合伙生意开始清算,打了几年官司的结果是要回来的布匹放满了整个四合院,据爸爸讲,连去厕所的过道都要侧着身子才能过去,把这些东西处理了,是够老姑姑和儿子娘儿俩一辈子生活费用的。可是,那年收留了不少过往拉骆驼的客人,年幼的大爷把喂骆驼的草给点着了,一场大火因此而起,一院子的丝稠布匹付之一炬。
就在前几年陪爸去包头看大爷时,哥俩聊起这个事,大爷仍自责地说,我就是个败家仔儿。我们都笑了,时过境迁,这些都成了故事。我们还去了乔家大院,乔家盛富之下,最大的功绩是,没有乔家,就没有现在的包头市。但是真实的走西口历程上的血和泪,要比电视剧《乔家大院》里多很多。
爸爸和二叔又说起一件事,那一年他19岁,在包头老姑家里遇见了老家来的一个长白胡子的老人,问老姑姑这个孩子是谁家的,老姑姑说是老家出来的哥哥家三小子。那老人家说那要是他家,他家不姓周,姓赵,这个小子的他太爷爷,满门抄斩时从京城逃命跑出来的,至于原因和名字,不知道。爸说曾经问过爷爷,爷爷说不知道(也许是不能说或许是老人没有告诉这个详情)。二叔说可能是真的,因为我家里从不提爷爷家,就住姥姥家的,所以周仁文爷爷才和我的爷爷那么亲,他们是在同一个姥姥家一起长大的。
声势浩大的回忆里放了太多的过去和秘密,讲到许多细节处,二叔和爸边说边擦眼泪,边互相凝望,并不时将手握在一起。因为担心爸心情起伏引发他的心血管病,也计划在山西四处看看,就别过了二叔一家,返回县城住下。临行时,给我们带了老家的蒸肉和香椿,我们也放下了从内蒙给他们带来的特产。第一次的认亲,就这样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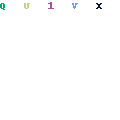
老家南王村南邻太行山,一出家门满眼的绿山头的太行山就横陈眼前,不由想起了那个子子孙孙都要移山的倔强的愚公。爷爷身上肯定是因为这股倔劲,才在走西口的路上一直走了下去,才有我们这些子孙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辈应该珍惜眼前的生活,珍惜拥有,才是我们最应该做吧!